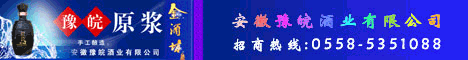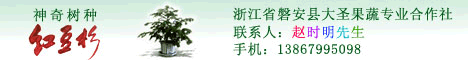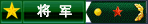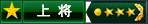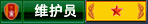第二十三回
军干部 细盘问追究根底
渔家妇 瞒身世自愿蒙羞
一大早,江婶的眼皮又老在跳。昨晚,她到江家宗公后堂客那里问来了真讯——她男人江水保在南京解放前夕帮一个国民党军官挑皮箱上了车。上车前,他托老乡捎了个口讯给江家宗公,说是把皮箱送上军舰就回家,叫芦生妈别着急。可是这么多年都没有消息,肯定是跟国民党去了台湾。
江水保这个剁头的,丢下我孤儿寡母不管了!江婶不由得又一阵心情烦躁。要是让人知道她娘儿俩是台属,有港台关系,那还了得!那就要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的!自己无所谓,那可就害了伢儿一生!
她向眼睑处‘拍拍’两巴掌,又从地上拣起一根稻草,掐了一小段,往上吐了口唾沫,贴在眼皮上——这眼皮跳得人心慌!菩萨保佑,让那没良心的露死露埋,免得连累我们整日里不得安宁。想到此,江婶不由得又一阵阵心酸——这么多年来,她第一次这么违心地咒骂自己的男人。
现在,江婶心里感到空落落的。俩伢都离开了自己,这还是第一次。打从收留了芦花,这女伢就从没有离开过自己一宿。倒是芦生,到江对过的彭泽县中学借读离开过家,那也只有两学期,以后,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
不知两个伢昨晚住在哪里?芦生的身子骨到底伤得怎样?江婶无心下地干活,就拿出针线,端出小竹椅,坐在门前,一边有一针无一针地纳芦花的袜底,一边不停地朝江坝上张望。
日上三杆。远远望去,阳光下,小孤山上的树木还是那样郁郁葱葱,生机盎然。不过,那些傍山依水的寺庙亭阁的白墙早已剥落,露出许多灰黑的斑块,许多飞檐翘角垂头耷脑,有些早不见了踪影,想必是掉进江里去了。从记事起,江婶从来没见小孤山如此衰败过。
“唉——这世道……”江婶不禁收回目光,摇了摇头,叹出了声。
倏地,一阵喇叭声响起,江婶望见一辆小汽车停在了江坝上,那车除了玻璃窗,全都裹着黄帆布。她知道,坐这种车的人一定来头不小。大军渡江那年,江坝上出现过这样的车,车上坐着戴大檐帽的国民党军官。打那以后,江婶就从未见过这种车。
仔细看去,从车上下来三个人,远远望去好象是当兵的,只不过没有大檐帽。“是解放军吧?”眼见得那三个人径直朝自己家走来,江婶不禁忐忑不安。
“就是这家。”一位穿着没有帽徽领章军装的人走在前面,指着江婶对另外两个人说。
那两个人倒是穿着得体的军装——草绿色的的确良军装配着鲜红的帽徽领章,显得格外精神。
江婶诧异地站起身,不知所措地瞅了瞅这些不速之客,习惯地拍了拍身上的粗布围裙,又望了望自家灰暗的茅屋门,见来者没有进去的意思,就堆起笑脸,讪讪地站在那里等着来者发问。
“你是江方氏吧?”那领路的是本地口音,一脸严肃。
“啊——是。”
“你是不是有个女伢叫芦花?”
“啊?是——”
“今年多大啦?”
“刚满十七。”
“是你亲生的吗?”本地人紧盯着江婶。
“你们这是——”江婶开始警觉起来。她疑惑地转过脸望了望另两位解放军。
“哦——是这样大妈,”一位满口京腔的解放军指了指本地人,“这是你们公社的余主任,您老人家别紧张。”
“我的伢,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怎么不是我亲生的?你这位同志真是——一句话说得人一笑,一句话说得人一跳!”江婶用不屑的眼光看了看那个余‘主任’。
“是这样的大妈,”那位解放军更加和气地说,“十七年前,也就是大军渡江前,您老人家是不是在江心洲收留了一个未满月的女婴?”
“什么?十七年前?江心洲……”江婶低头沉吟,再也不正面回答来人的问题了。
“对!您老人家收留了一位国民党军官夫人刚生的女孩!你知道吗?那对夫妇是地下工作者……”问话的人进一步开导着。
“什么什么?国民党?!”一听此话,江婶立即既害怕又紧张起来。这些年,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社教,四清,文革。国民党反动派,地富反坏右全部揪出来示众,有港台关系的更是不会放过。村前村后,乡里乡亲一律分成红黑两类,莫不是他们知道芦花的身世,要把她划成黑五类的‘狗崽子’?那就害了我的伢啦!
顿时,江婶毛骨悚然,一股凉气直冲背脊沟,紧接着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她站在那儿,只觉得眼前一阵阵发黑,头昏眼花,天旋地转。
“呃呃,大妈!您怎么啦?”两位解放军见江婶站立不稳,赶紧扶着她坐在门口的小竹椅上。
好一阵,江婶吃力地睁开紧闭的双眼,缓过神来,深深叹了一口气说:“唉呀,你们、你们莫编那些骇人故事吓我了!把我吓死,我那两个苦命的伢靠谁呀?呜呜——”显然,江婶在故意转移话题。
“嗨!你别哭。江方氏我问你,你家芦花是哪年生的?”余‘主任’问。
“哪年生的?大军过江那年哒!”江婶不假思索地说。
“据我所知,你男人一九四七年底就被抓壮丁走了,后来就杳无音信,他人不在家,你怎么会生孩子?怎么有了芦花?”这位余‘主任’冷笑着问。
“芦花、她、她是遗腹生……”江婶不善谎言,支吾着说。
“那她比芦生小几岁?”
“小两岁。”
“这就对了!难道你不是十月怀胎,而是怀了两年?!”余副主任好象抓到了把柄。
“你!?你真是吃海水管‘闲’事!我们女人家的事,你们男人懂什么?你管我怀了多长时间?反正芦花是我亲生的。不是亲生,我能屎一把尿一把把她养大?!”江婶横了余‘主任’一眼,起身要进茅屋。
“呃呃!大妈,有话好说,您老别生气。”一位解放军拦住了江婶,“我们这次来,是奉了我们首长,也就是军区后勤部齐部长的指意,寻找他的女儿芦花的。当时首长是地下……”
“我不管什么手掌脚掌天上地下!反正芦花不是捡来的,是我十月怀胎生的!”江婶斩钉截铁地说。
“你刚才还说怀了两年!你这个人、你这个女人怎么前言不复后语?你看看——”余‘主任’对解放军说“她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他强忍一肚子窝火,紧盯着江婶,无奈地说,“江方氏,你怎么这么不老实……”
“我怎么不老实啦?芦花是我生的,这一带四乡八邻谁不知道?”
“那——你丈夫不在了,你怎么能生?”
“是我偷人养汉生的!你能把我怎样?!”江婶突然满脸红涨,一边用手拍打着胸膛,一边逼向余大船,“你们把我抓去坐牢吧!我们江方家祖祖辈辈穷苦人家,贫下中农,你们看着办吧!我正是活得不耐烦了!”
一时间,江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不再是温和的渔家妇女。她用手拢了拢花白的头发,仰首阔步,眼光咄咄逼人,进一步向余大船逼去。吓得那余‘主任’步步后退,一个趔趄,差点跌了个仰面朝天。
“哎呀大妈,您老人家别生这么大的气。”那位解放军见事情闹僵了,开导着说,“您总不能让芦花跟您吃一辈子苦吧?”
“穷人家的伢儿,苦菜花的命,不想过洋日子!”
余大船也变了口气:“江方氏,您是明白人,放着有福不让芦花享,您这当妈的忍心吗?哦,对了,芦花呢?这女伢长得怎样,让这位同志看看象不象齐部长?”
“我的伢出远门了,怎么?难道你们还想抓她不成?!”江婶根本不相信这余大船。
“哦,我想起来了!为了抚养孩子,当年齐部长还给你不少金银首饰。据首长讲,那些东西是用一顶国民党军队的大檐帽装的。”为了取得江婶的信任,那位解放军和蔼地说。
一听说到金银首饰,江婶更不敢承认芦花的身世了。当年,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到处烧杀枪掠,那些金银首饰,说不定是那个姓齐的‘刮民党’的不义之财!
“你们越说越蹊跷了,我没有闲工夫听你们的鬼话!请你们走——”江婶转身进门,“哐”地一声,她把两扇破木门插上木栓,再也不理睬门外的人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5-12-25 9:59:21编辑过]

 Post By:2015/12/22 7:39:08
Post By:2015/12/22 7:39:08


 Post By:2015/12/22 7:40:22
Post By:2015/12/22 7:40:22




 Post By:2015/12/23 9:54:20
Post By:2015/12/23 9:54:20




 Post By:2015/12/25 9:58:43
Post By:2015/12/25 9:58:43




 Post By:2015/12/26 8:07:36
Post By:2015/12/26 8:07:36


 Post By:2015/12/27 10:11:42
Post By:2015/12/27 10:11:42




 Post By:2015/12/29 6:16:34
Post By:2015/12/29 6:16:34


 Post By:2015/12/29 9:49:54
Post By:2015/12/29 9:49:54




 Post By:2015/12/30 6:53:39
Post By:2015/12/30 6:53:39




 Post By:2015/12/31 11:02:49
Post By:2015/12/31 11:0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