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更人
童年时,我最喜欢听到的声音是“梆、梆、梆”的打更声了,这声音伴着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上个世纪的70年代中后期,少年的我离开了它外出求学去了。当再回来想听到它的时候,它却永远地离开了我——更夫业已故去,也没有了后继者,“梆、梆、梆”的更声从此没了,小街似乎安静了许多,却失去了小街应有的风采,人们少了对夜晚时间的判定,却多了很多对更声的期盼与回顾。
更夫潘姓,公称潘爷,是一个终生寡居的男人,和我家对门错开三四家。儿时的我经常在他门前玩耍,他有两个兄弟,却不太多来往。我记事时他好像就有快六十岁了,和我爸爸差不多高(1米7多),背,有点微陀,瘦瘦的。打更也是街道(现在说是社区)照顾性质的,每月好像也只有十几块钱,但他却做得很认真。每晚的八点钟左右都准时地响起“梆、梆、梆”的更声,是为一更,然后是十点钟左右的二更,十二点钟左右的三更,凌晨两点钟左右的四更,凌晨四点钟左右的五更。每更都是绕街道或“关键部位”一圈巡防,不论阴晴雨雪、常日假日,一切如旧,而且十分准时。那时的人们家里很少有钟的,更不要说手表了,人们夜间对时间的判断,只是依据更声了。大人催小孩回家睡觉,就说,潘爷马上要打二更了(快夜里十点钟了)。小街上有一句谚语说一个人守信,就说:“你和潘爷的更声一样准”。有次潘爷病了,连走路都没有了力气,硬是找我爸爸帮他去公社(乡政府)请假,不过五更时还是听到了更声,后来我爸爸问他为什么会这样时,他说,后半夜好了不少,能打一更还是打一更的好,我是打更的,更没打,就是白吃了一天的饭。
他的生活很清贫的,日常伙食少有荤菜,一点米饭就着点蔬菜或咸菜就打发了他许多的日子;不抽烟不喝酒,与人不争高下,见到谁,哪怕是小孩都是客客气气的;身上穿的衣服是穿过许多年的了,破了,自己补补,有时隔壁的杨姓裁缝也帮他补补。衣服虽旧,但是洗的非常干净,穿得也非常干净。他的家当,值钱的大概就是一个闹钟了,放在最保险的条台上,那是他的工作依据,也是我们这条小街夜间的标准时间。还有一个手电筒,是装三节电池的那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是舍不得用的,他平时夜间打更时用的是马灯,点煤油的那种,费用很省的。这些都是公社(乡政府)发的,他用得十分的仔细,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六七年都没有换过。那闹钟,我知道是修理过几次的。打更的梆子是用一截很大的毛竹做的,敲打的棒子是一种很结实的木头做的,结实的木棒敲打在毛竹筒上就有了我儿时的小夜曲:“梆、梆、梆......”,有时候这更声也是有一定节奏的,如:绑、绑绑、绑等,打更时也有时令的提醒语句,如:“梆、梆、梆”,天干物燥,柴草离灶,各家各户,火烛当心......
故去的潘爷,老街坊还是常常怀念他的,但是老街上几乎全是新人了,新人没有享受过潘爷的更声,也就不知道潘爷了,潘爷也就渐渐地淡出了小街上人们的视线。
这样的清平,这样的装备,这样的打更人,过去的小街,在更声中甜美地睡去,那时的孩童却在更声中不知不觉地已经长大。可现在,回乡的我还是我,可潘爷不在,更声不再为我、为这条小街、为守护许多童年的梦——敲响!
我怀念儿时小街上夜间的更声,我怀念那打更的潘爷,那更声始终在我的心里回响——做一个和潘爷更声一样准的人——虽然有差距,但是我会很努力的。
注:
这点文字是我2010年1月1日的一篇博文,有修改。文字码得不好,但本人情真意切。请斧正。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2-8 11:54:57编辑过]

 Post By:2012/2/8 11:52:35
Post By:2012/2/8 11:52:35


 [本帖被加为精华]
[本帖被加为精华]

 Post By:2012/2/8 12:00:46
Post By:2012/2/8 12:00:46




 Post By:2012/2/8 12:30:57
Post By:2012/2/8 12:30:57




 Post By:2012/2/8 13:41:22
Post By:2012/2/8 13:4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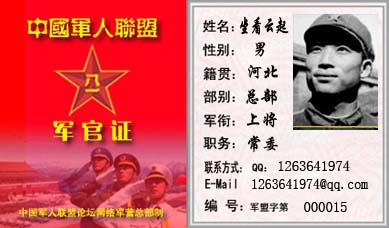


 Post By:2012/2/8 14:20:05
Post By:2012/2/8 14:20:05




 Post By:2012/2/8 16:04:13
Post By:2012/2/8 16:04:13




 Post By:2012/2/9 9:02:14
Post By:2012/2/9 9:02:14




 Post By:2012/2/9 19:53:47
Post By:2012/2/9 19:53:47




 Post By:2012/2/9 21:02:03
Post By:2012/2/9 21:02:03




 Post By:2012/2/10 18:57:16
Post By:2012/2/10 18:57: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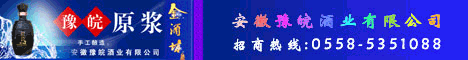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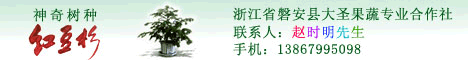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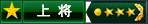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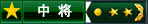

 金沙湖好文笔!
金沙湖好文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