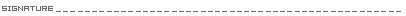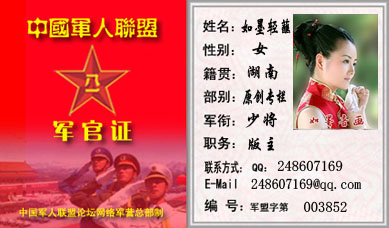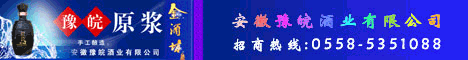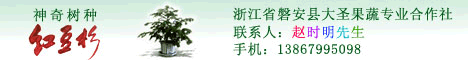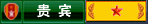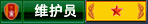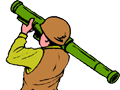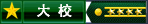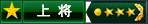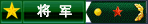在精神文明方面,嵩山地区的先民不仅创造了文字、礼乐和一系列文学艺术成果,而且形成了独特的宇宙观、社会观、道德观。从贾湖遗址所发现的契刻符号,到仰韶文化器物上出现的各类符号,从郑黄寨夏代刻文甲骨的出现,到安阳上万片商代甲骨文的出土,中国成熟的文字体系在嵩山地区创造完成。中华元典文化中《诗》《书》《老子》,以及理学、神宗佛学等,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敬天法祖的历史观,道法自然的社会观,尚中贵和的天下观,自强不息的人生观,仁义诚信的道德观,很多都与创生于嵩山地区的诸子思想相关联。
在制度方面,夏朝开启了家天下王朝体制,置军队,定“禹刑”,划“九州”。商朝创立了分封制,细化刑法,完备军队。周朝强化了礼制。隋炀帝在洛阳初创科举考试制度,武则天在东都洛阳开殿试,创武举,科举制遂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拨方式,对历史发展产生了广泛且深刻的影响。
以龙为主图腾的文化认同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重要表现。距今6000多前的蚌塑龙,是嵩山地区最早的龙文化遗迹,此后二里头遣址中出土的绿松石龙,安阳殷墟出士的绿松古龙,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盘上的蟠龙纹,殷墟亚长墓中出土的玉龙,都反映古代先民对龙的信仰一脉相承。
《史记》等文献记载,黄帝部族统一中原后,黄帝活动的地域很广,但大多数集中在中原地区,其核心地区在今河南新郑一带,并在新郑建有熊国,彊域“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洞、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中国古代“大一统”体制至此逐步确立,对华夏、中国的认同以及绵延数千年的家国情怀也由此肇始。
“中”的理念形成“治者必居其中”的政治传统。国家统一,居“天地之中”而治,“得中原者得天下”等理念,成为统治者对国家中心择选的重要因素。正所谓“欲进四旁,莫如中央,故王君必居天地之中”。历代王朝多建都于以嵩山为中心的地区。中国著名古都,嵩山周边有其四(郑州、安阳、洛阳、开封)。古代历史上众多帝王国都之所以选择在嵩山封禅祭祀,正是旨在假嵩山祭祀天地大典,彰显“大一统”政治的“正统”和强盛。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主要体现在文化融合、民族融合两方面。嵩山地区文化的包容性实例俯拾皆是:如嵩山地区裴李岗文化强势辐射不仅使得黄河、淮河流域文化彼此连接而且使得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也有了不少共性,产生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又如距今6000左右,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彩陶在东北方向一直影响到西辽河流域,使得红山文化中开始出现黑彩和类似花瓣的彩图案,向东影响到山东和东南沿海,大文口文化和松泽文化也都出现了花瓣纹彩陶同时也渗透到湖北、湖南和重庆大溪文化。庙底沟时期仰詔文化扩大影响到西至甘、青,北到内蒙古中南部,东到海岱,南到潇湘,形成了“中国早期文化圈”。
嵩山地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体现在距今5000年前从西亚经中亚和我国西北传入中原的小麦、黄牛、绵羊,以及冶金术。南北朝禅僧菩提达摩在嵩山少林寺创立顿悟成佛的禅宗。在嵩山之巅,著名道观中岳庙、禅宗祖庭少林寺与嵩阳书院,“三教”荟萃,和谐比邻,彰了文化的包容与融合。
从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始,经夏商周春秋战国到秦汉,第二次民族大融合促进了华夏共同体的发展和汉族的雏形。在第二次民族大融合过程中,三国两晉南北朝时期的鲜卑、吐谷浑、柔然,随唐时期的突厥、吐蕃、回鹘等游牧民族或不断吸收中原文化,或群体性迁入中原,为汉文化输送新鲜血液,最终形中华民族共同体。
和平性,本身就蕴含着平等、平和、中和、和合之意。嵩山地区很早就形成了“中”的理念与“中和思想”,为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孕育了“文化基因”。“中和思想”是由“中”与“和”两种理念结合而来的复合性哲学范畴,《礼记》将“中”与“和”并称合用:“喜恕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到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思想”之所以上孕育于嵩山地区,既与华夏先民和善、凝聚、协作的氏族性格密不可分,也与“天地之中”的观念有内在关联。在文明起源的过程中,人们关注天时,顺应自然,注重和合相生的合作理念。
上古舜帝曾“求中”于“鬲茅”(今濮阳。荷泽一带),而商祖上甲微为夏禹“求中”于嵩山,西周初年周公在嵩山测影“立中”。嵩山地区特有地理环境,以及中和思想的整体观,实际上是天地之中“文化基因”的传承和演化、《周礼》等记述的“天地所合”“四时所交”“风雨所会”“阴阳所和”“道理所均”这是一个在多数文化因素作用下形成的东方宇宙观,并逐渐发展为“中和”“中正”“和合”等思想。“和生万物”的世界本源观、“天人合一”和谐共处观、“过犹可及”的居中平衡观、“和而不同”的共生共赢观,一同构成中国思想史上“中和思想”体系,逐渐成为中国人民的做事准则和处世标准,用以处理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体现为“平等相待”“和平共处”。
2024年11月13日

 Post By:2025/3/15 14:39:43
Post By:2025/3/15 14:39:43


 Post By:2025/3/15 14:42:03
Post By:2025/3/15 14:42:03


 Post By:2025/3/15 17:39:48
Post By:2025/3/15 17:39: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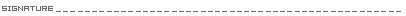



 Post By:2025/3/15 17:47:54
Post By:2025/3/15 17:47:54


 Post By:2025/3/15 21:45:56
Post By:2025/3/15 21:45: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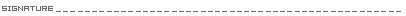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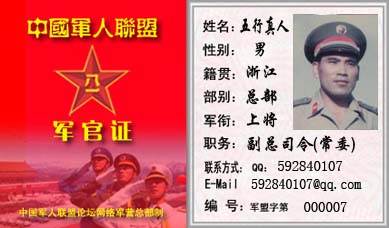


 Post By:2025/3/15 21:55:52
Post By:2025/3/15 21:55:52


 Post By:2025/3/16 14:40:42
Post By:2025/3/16 14:40: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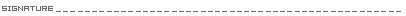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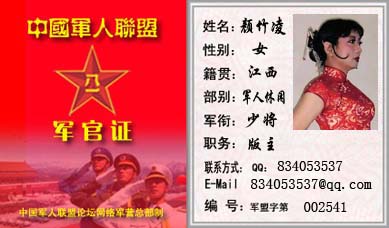


 Post By:2025/3/17 16:55:00
Post By:2025/3/17 16:55:00


 Post By:2025/3/17 22:26:30
Post By:2025/3/17 22:26: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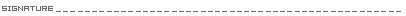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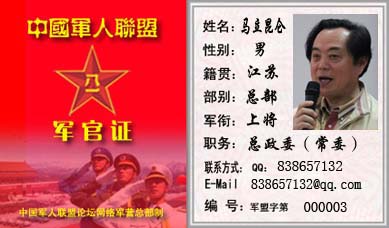


 Post By:2025/3/18 17:34:23
Post By:2025/3/18 17:3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