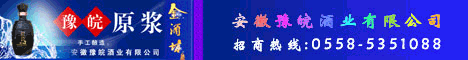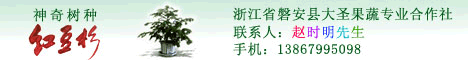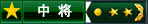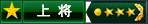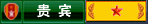两个人急忙上得江堤,向出事的那边望去,不禁大吃一惊——
一头大水牯牛疯了一样冲入一条又长又阔的泄洪渠里,拼命地向对岸蹬踏游动着。对岸,一条水牝牛正悠闲地吃着草。这水牝毛色油光发亮,丰满浑圆的屁股上,一条漂亮的尾巴象在炫耀似的不停地摇摆。这使得水中的水牯盯着它,更勇往直前。游到水中央,这水牯好象很吃力,只剩一对圆圆的鼻孔露出水面,不时喷出尺把高的水珠。仔细看去,原来牛脖子上还紧紧伏着一小女伢!只见她双手死死拽着牛耳朵,惊恐地哭叫着。那牯牛早失去了往日的温顺,一边不停地摇晃着脑袋,想甩掉骑在它颈脖上的小女伢,一边拼命地向泄洪道对岸蹬踏,无奈那岸又陡又滑,一双前蹄不时被烂泥陷住!
眼看小女伢马上就要被水牯甩入水中,万一再被牛蹄蹬踏,那就更危险!芦生取下膀子上的吊布,不顾一切地跑下江堤。他知道,这泄洪渠水深三四米,因多年没放水,水底已全是烂泥。一旦那牛筋疲力尽,不仅小女伢危险,连那牛自己也有被陷的可能。
他边跑边观察着,知道水牯是被对岸的水牝吸引才这样不顾一切的。只可惜这水牯是剃头挑子一头热,那水牝牛还是那么悠闲地吃着草,对近在咫尺的水渠里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
芦生不顾芦花的拉扯阻拦,快步跑到渠道边,跳入水中,向水牯游去。他尝试着用两手捣水,但,那受伤的右膀还是不能自如活动。不过,凭着他过人的水性,也很快接近了那你牛牯。
“别怕,别怕!小妹妹,快下来,哥哥接你。”他双脚踩水,伸出左手。
慌乱中,小女伢松开了拽着牛耳朵的一只手,让芦生牢牢地抓住后,才慢慢松开另一只手,一下子扒在芦生肩膀上,就紧紧搂住他的脖子。
“好了好了,小妹妹,没事啦!莫搂我的颈,对,抓住我的肩膀,昂起头,对,这样就没事。”芦生强忍着疼痛,让那小女伢紧搂着自己的右肩,一边亲切地说着,一边用左手划水。
很快,芦生把小女伢推上岸,那芦花连忙接住。芦生靠在岸边喘了几口气,又扑进水里,向那水牯牛游去。
那水牯身上减轻了负担,又加快了蹄子的蹬踏,一心只想爬上有水牝的对岸。只可惜烂泥陷脚,就是上不去——真可谓老牛跌进烂泥坑,有劲也翻不了身。
“哥——,别靠近,危险!那牛猖疯啦!”芦花高喊。
“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它朝对岸哞哞叫起来,在岸上来回疯跑几圈,我来不及下来它就冲进了水里。”被救上来的小女伢惊魂未定地说。
正当芦生在水牯旁游移,无法靠近之际,苇香不知什么时候绕到对岸,将水牝牛牵着,沿岸边慢慢向下游走去。这水里的牛牯立即调转身,跟着向下游游去。
这泄洪道,越到下游水越浅,最后呈扇状与两边的田畈连成一片了。
水牯牛脱险了,爬上岸就向水牝奔去,把通红通红的牛鞭伸出老长,笨拙地往它的‘至爱’身上扒。放牛娃们对牛‘做那事’早司空见惯,丝毫不感兴趣。他(她)们围着芦生,充满感激之情。芦生对围拢上来的一个稍大点的放牛娃说:“等它们亲热过后,你把水牯头上的绳索解开,交给小妹妹。
“好喽!”孩子们一阵欢呼雀跃。
“好哥哥,多谢您!”那被救的小女伢拉住芦生的手,久久不放。一双大眼扑闪扑闪已不见了惊恐。
“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芦生笑着,摸了摸那小女伢的头说。
“我叫芦花。”
芦生和芦花相视一笑。
“你也叫芦花?”大芦花亲切地抚弄着小芦花的头问。
“恩。姐姐,你跟哥哥真是好人!今天,要不是这哥哥,我和牛都没命了!我淹死了不碍事,这牛是生产队的,要是它奔命淹死了,不知该咋赔呢?”小芦花只穿了个小抹兜,把湿花褂子晾在头上,牵着两人的手,舍不得放松。
“芦花妹妹,你吓着了吧?回头叫你家里的人来这里叫个魂吧。”大芦花搂着小芦花,亲切地说。
话刚落音,一个男孩就抢去小芦花的花褂子,说:“现在就叫!”他把那花褂子搭在一把干枯的荆棘上,拖着,一边沿岸跑,一边高喊:
“芦花嘞——,吓脱魂莫怕来家吃夜啰!”
“芦花嘞——,吓脱魂莫怕来家困醒啰!”
“好!小芦花,那哥哥在给你叫魂去惊吓,你去应吧!我们还有事要过江呢。”
那小芦花就前去“来着喔——来着喔——”地跟在那搭着湿花褂的荆棘后应答着。
此时,德圆和邱志鹏忽然出现在人堆里,“你们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还过江么?那渡轮早回去了!”邱志鹏埋怨说。
他俩还带来一个坏消息——虽然找到了藏佛首的沙坑,但是那佛首却不翼而飞了!直惹得芦生懊悔不已。
直到夕阳西下,最后一班渡轮才姗姗来迟,吐下了几个江北人。芦生芦花和邱志鹏正要上木跳板,江坝上突然传来一阵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和喊叫声——
原来,被黄鸭蜂蛰得头浮眼肿的余洪水只在公社卫生院敷了点草药,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医生说,卫生院没有药物保护病人的肾脏,防止肾衰竭,也没有冷敷的条件。为了抢救他,余大船派一个赤脚医生跟吉普车到码头,也要到对江的彭泽县医院去。
一行人就急匆匆护拥着余洪水上了渡轮。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2-9 8:08:55编辑过]

 Post By:2010/12/7 10:42:12
Post By:2010/12/7 10:42:12


 Post By:2010/12/7 21:01:28
Post By:2010/12/7 21:01:28




 Post By:2010/12/8 11:26:59
Post By:2010/12/8 11:26:59




 Post By:2010/12/8 14:56:15
Post By:2010/12/8 14:56:15




 Post By:2010/12/8 18:31:14
Post By:2010/12/8 18:31:14




 Post By:2010/12/8 18:35:07
Post By:2010/12/8 18:35:07




 Post By:2010/12/8 18:36:28
Post By:2010/12/8 18:36:28




 Post By:2010/12/8 18:37:24
Post By:2010/12/8 18:37:24




 Post By:2010/12/8 20:54:27
Post By:2010/12/8 20:54:27




 Post By:2010/12/9 10:51:48
Post By:2010/12/9 10:5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