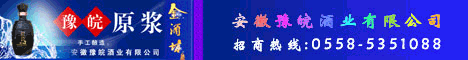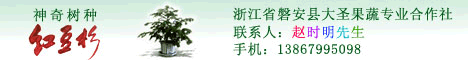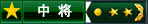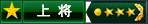苇香从门背后出来,一把揪住德圆的耳朵,“你答应啦?”
“答应什么?”德圆装糊涂。
“你不要命哪!那余大头上次不是送医院送得快,早见阎王爷去了。你有什么能耐,敢去捅马蜂窝!?”苇香说着,一屁股坐在地门槛上,心烦得想哭。她想不到自己居然这么命苦,好不容易有一个男人可以依靠,可以疼自己爱自己,却眼睁睁看着他又要去闯鬼门关!她知道,这德圆虽然没有大的本事让自己衣食无忧,但他为人憨厚老实,吃苦耐劳,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我、我是为了芦花,为了芦花的亲生母亲才答应的嘛……”德圆挠着光头说,“没有那么严重吧?蜂子蛰一下就没命?”
“是你跟芦花亲还是我跟芦花亲?这事根本与芦花家不相干!”
“是不与她们家相干,可是人家芦花妈……”
“人家芦花妈就那么馋?非要拿人命去换那几串葡萄?你脑子进水了是吧?这是余大头要暗算你!你还当真他们是为了那些客人……”
“怎么办?我要是不干,那余大头会变本加厉地害我们的。你说过,他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这下,这小和尚感到事情严重了。他也坐在门槛上,两个拳头一个劲地捶自己的脑袋,急得也要哭。
一会儿,他忽然一把抱住苇香说:“事到如今,只有硬着头皮干了!好姐姐,倘若我有个三长两短,你好歹用个芦席把我卷了,埋在你那撒网打鱼的男人一起,好吗?你给他上坟时,也顺带给我上一炷香,也算我俩恩爱一场……”
“放你的东风狗臭屁!好个没有出息的小秃驴!你再说这些丧气的话,看我不撕烂你的舌头!”苇香忽然杏眼圆睁,抡起巴掌就要扇过去。
德圆抱着头躲开,哭丧着脸蹲在那儿,再也不敢语言了。
“丧门星,你刚才说我男人什么来着?”苇想略有所思。
“撒网打鱼呀。”
“撒网打鱼?对,我有办法啦,德圆,我有办法啦!”苇香忽然手舞足蹈,原地打起圈圈来。
德圆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没事吧?好姐姐。”他小心翼翼地问。
苇香一把抱住德圆,“一切听从我安排,保险把那屋顶上的葡萄全部摘下来!你在这里等我——我回趟娘家!”
说完,那苇香就飞也似的下山去了。
断黑时分,苇香气喘吁吁上山了。德圆迎上去,见她背了一个大包袱和一个鱼篓,赶忙从她背上卸下那包袱,“你这是——”
苇香笑嘻嘻地对德圆说:“走,进屋去,我告诉你怎样对付那些黄鸭蜂!”
两个人在屋内叽叽咕咕说着,直惹得德圆拍手打掌笑个不停。
“早点睡吧,明天要起早,今晚可不能再做那事哦。”苇香哄着德圆说。
天刚蒙蒙亮,这一对男女就起来了。门开了,只见那德圆穿着渔民冬天打鱼的皮衣皮裤,手戴皮手套,脚蹬皮靴,头上套着个猪肚帽。那帽子罩下来,蒙住了整个脸,只露出两只眼睛。苇香又让德圆戴上一副防风镜和一顶三块瓦的棉帽,背上鱼篓。两个人慢慢向启秀寺走去。德圆这一身行头,使苇香暗暗好笑——我那短命的打鱼郎,你留下来的东西,我今天总算派上用场啦!
看着德圆武装整齐了,苇香笑着说:“好啦,看那些蜂子能把你怎样?我去扛梯子。”说着,一溜烟把长长的梯子扛过来,稳稳地架在启秀寺先月楼耳房的山墙上。
“苇香,我上去啦,你自己要躲远点哦!”蹬梯子时,德圆吩咐苇香。
“我知道,你尽量不要扯动葡萄藤,篓子里有剪刀。”
那德圆像一个登月的苏联航天员,慢吞吞一步一步上去了,苇香扶着梯子,见他上到了屋顶,就大声说:“你慢慢来,不要慌,我到屋里去。”
上得屋顶,只见已经有些枯黄的叶子下,硕大透明的葡萄一串串遍屋顶都是。德圆喜出望外。为了慎重起见,他蹲下身,用眼睛寻视一下周围着,不禁紧张起来——
那马蜂窝近在咫尺,挂在天窗的木框下,足有一个小葫芦那么大。晨曦中,许多蜂子正爬进爬出,有的正在抖动着翅膀,看样子是等翅膀上的薪露干了再起飞。
德圆不由得又把猪肚帽向下拉了拉——这是他全身防御能力最薄弱的地方,然后小心翼翼地从篓子里取出剪刀,轻手轻脚把身边的葡萄一串串剪下来,装进篓子里。
太阳起山了,那些黄鸭蜂潮湿的翅膀大概也干了。不知道是通过眼睛,还是通过气味,它们发现自己的领地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于是,一场‘领土保卫战’开始了!
开头是小股袭击,轮番出动。见来犯者岿然不动,就开始了更大的行动——它们倾巢而出,在来犯者前后左右,上上下下,天上地下来了个‘立体进攻’!
那德圆开头还无所谓,一门心思剪他的葡萄,见这些蜂子太猖狂,竟爬到他的防风镜上,把视线挡住了!惹得他无名怒火顿起,几下爬到天窗前,用剪刀把那马蜂窝剪下来,站起身,喊了一声:“苇香,你不要出来!”就把那窠蜂子的老巢朝山下长江里丢去!
这下好了,端掉你们的老窝,没有后顾之忧,年年都可以上屋顶摘葡萄了!德圆在猪肚帽里不由得自个儿笑出了声。

 Post By:2010/12/14 12:33:38
Post By:2010/12/14 12:33:38


 Post By:2010/12/15 9:10:48
Post By:2010/12/15 9:10:48




 Post By:2010/12/15 9:12:00
Post By:2010/12/15 9:12:00




 Post By:2010/12/15 9:43:48
Post By:2010/12/15 9:43:48




 Post By:2010/12/16 8:40:50
Post By:2010/12/16 8:40:50




 Post By:2010/12/16 8:42:35
Post By:2010/12/16 8:42:35




 Post By:2010/12/16 8:43:33
Post By:2010/12/16 8:43:33




 Post By:2010/12/16 8:49:38
Post By:2010/12/16 8:49:38




 Post By:2010/12/16 8:50:14
Post By:2010/12/16 8:50:14




 Post By:2010/12/16 10:58:57
Post By:2010/12/16 10:58: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