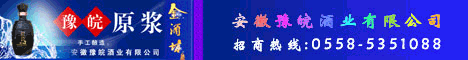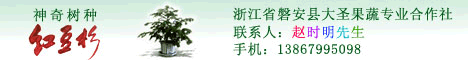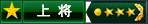第七十四回 一封信 引出来港台关系
两个人 找到了确凿证据
芦花回来,并没有住进彭泽县人武部宿舍大院她的新房里,而是依旧回到小孤山下那三间平房,回到江婶身边。
“芦花,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你不能老是住在娘家呀,我把你系在我身边,你婆家会埋怨我的。”江婶劝芦花。
“妈,那邱志鹏又不在家,我住在那边,整天肩不挑,手不提的,闷得慌。你就让我在这边陪你吧。”芦花依偎在江婶身边,还是像原来一样亲昵。
“那,你得依我一条,不准下大田干活!”江婶说。
“好好!妈,依你,只要不赶我走。”芦花一边说,一边把挂在堂厅正墙上的她和芦生合影取下来,把灰尘抹掉,看着那相片愣神。
江婶看在眼里,顿时心里一阵难过,就说:“花,我的好伢!婚姻都是前世所定,你再也不要把以前的事搁心里。妈知道你的心思,可是,事到如今,你只好认命吧!”说着,把那相框接过来,看着芦生的照片说:“你呀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怎么就……”
只说得芦花眼泪哗哗,娘儿俩就又抱着痛哭一场。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一个天色暗淡的日子,厚厚的乌云老是遮住那要露头的日头,风却帮不了一点忙,满天的荫霭不散——好像一阵暴风雨就要来临。
一阵自行车铃声响起,从田畈上走过来被撤职看大门的余大船。他走到江婶家门前,就大声喊:“呃——屋里有人吗?快出来!”
芦花和江婶应声而出,见是余大船,江婶问:“哦,是、是余主任,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啦?”乡下人,哪怕你只当了一天官,也改不了口。
“呃,不要再叫我主任啦,看大门就看大门,没有什么了不起!秦琼还有卖马的时候,这年头,当官像台上演戏一样,保不准谁能红一辈子?”他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封皱软的信说:“看不出啊,你家还有港台关系!你看看,江水保是不是你男人?江方氏是不是你?”
江婶就一把接过来,递给芦花:“看看——是不是寄错了?我男人是叫江水保哇!不过同名同姓,寄到我家来了,蹊跷事也不能说没有!”
“按道理不错!江水保是你男人吧?那还能看错——”那余大船说完,冷笑一声,转身扬长而去。
“妈,这信好像被人拆过呢。”芦花把信拿在手里,见信的封口不对头,“你看——
“唉,不管,你先念念!”
芦花就从里面抽出信纸,一字一句慢慢念起来——
“爱妻江方氏,见信如见面!吾自离开大陆,漂泊到台湾已有二十五年。因两岸隔绝,信息封闭,终不得妻与爱子之音信。今因商务赴港,歇息之夜,特书简信一封,聊表思念之情!想必吾儿已二十有七了,已近而立之年。而吾日渐年迈,身体衰弱。孤身商旅之日,夜深人静之时,想起台北略有薄产,竟无有后继之人,繁忙商务,也无人助一臂之力,不禁哀叹!尚能收此书信,务必按此信所书地址回复,必能辗转台北,吾将欣喜万分!丈夫江水保。”
“你仔细看看,是不是江水保三个字?”江婶半信半疑。
“是呀!千真万确是江水保,这三个字最好认呢。”芦花说。
这封信,芦花念起来很吃力,但意思却相当明显,就是说,江水保没有死,还活着。不仅没有死,还有一笔财产,这让江婶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的丈夫总算有了确切消息,说不定有生之年还能见面。忧的是,自此,让人家知道她江婶家有港台关系,不知道是福是祸?至于那‘略有薄产’没有使江婶动半点心。
“这个路死路埋的,年纪大了,身子动不得了,就想起了我娘儿俩……”江婶不由得又鼻子发酸,“保不定是娶了年轻的洋婆子,见他年岁大了,掏空了身子,把他一脚踢了呢!”
“妈,这事要不要让哥哥知道?”芦花问。
“那哪能?那不要了他的命!当兵时说过他父亲江水保已经身亡,现在又突然冒出个父亲来,叫他怎样向组织交代?还是不让他知道为好,不知者无罪过!”
“嗯,也是。”
“唉!那江水保还不如死了好……”江婶心里像蒙上了一层阴影。
是夜,娘儿俩早早上床,却久久不能入睡。

 Post By:2011/1/31 23:45:48
Post By:2011/1/31 23:45:48




 Post By:2011/2/4 9:15:45
Post By:2011/2/4 9:15:45




 Post By:2011/2/7 21:18:05
Post By:2011/2/7 21:18:05




 Post By:2011/2/8 8:30:21
Post By:2011/2/8 8:30:21




 Post By:2011/2/8 8:34:17
Post By:2011/2/8 8:34:17




 Post By:2011/2/8 20:10:14
Post By:2011/2/8 20:10:14




 Post By:2011/2/9 14:05:43
Post By:2011/2/9 14:05:43




 Post By:2011/2/10 9:29:36
Post By:2011/2/10 9:29:36




 Post By:2011/2/10 9:31:52
Post By:2011/2/10 9:31:52




 Post By:2011/2/10 9:35:00
Post By:2011/2/10 9:3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