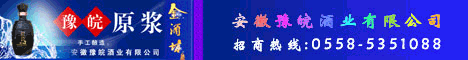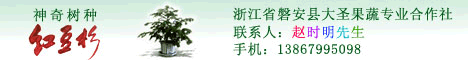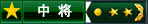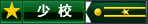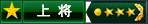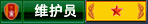《 北方的炕 》
——舒心
北方有热炕,这是北方人的福气,现在但城里没有,有的是乡下。我夫人家就有,和照片上的一样,乡下冷,冷得干烈。不高的院墙和不密闭的门,挡不住风。风从空旷的土地上一路横行,无拘无束。那是一种高傲的姿态。遇到村庄时,它的情绪被打乱了,乃至有些恼羞成怒,于是,狠命地撞击着门,撞击着墙。门和墙结实着呢,那就从门缝里乘虚而入。
乡下来了客人、亲戚,就得上炕。不是什么规矩,庄户人没那么多规矩。不是非上不可,但屋子里冷得坐不住,也站不住。脱了鞋,上了炕,用被子捂住腿和脚,就不冷了。
炕贼热,有时烧屁股,时间久了,得挪挪或者抬抬,要不就成猴屁股了。一家人围着,来了客就和客人谝着,家长里短,说说笑笑,拉弄是非,这些工作都在炕上完成。
炕是冷不下来的。乡下有的是麦草。麦草被点着,搡进炕洞,把炕门堵上。麦草因为缺了氧气,窒息,开始挣扎,无精打采地活着。放心,“死”不了,炕门并非密不透风,稀薄的空气基本可以保证麦草苟延残喘。这是最佳状态。炕被熏热了,还省了麦草。
炕洞里没火,有烟。烟如人满腔的豪情,顺着烟囱往天上撺。浓密,却不黑。不黑就没了污染。冬天的乡村虽然家家都烧麦草,但院子里从不落黑尘。麦草是纯朴的,如麦粒的纯朴,如庄稼人的纯朴。
淡淡的烟味儿一定有。闻多了就习惯了。还觉得挺香。麦草烧出的烟味儿比其他烟味儿一定香。那烟味随着热炕清晰地笼罩着人的全身。大人们说着话,小孩子们闹着。孩子们累时,顺势倒在母亲怀里。母亲的怀是热被窝,孩子们做着一个又一个梦,间或在被窝里放个小屁,母亲就笑了,嘴上说,这孩子,手在圆圆的小屁股上揉两把。孩子们翻个身,又徜徉在梦乡里。
炕热时热,冷时也冷。白天不明显,晚上就晓得了。到后半夜乃至快天亮时,身下还有温度,但脚下就很冷。这和麦草的余烬有关,也和炕的散热有关。脚冷还有被子捂着,头却始终是暴露的。头的温度基本等同于房间里的温度。庄户人的门不讲究,有缝,甚至大得很;也不保温,是木板子“凑合”的。头就冰冰冷冷的。人的头最不娇贵,原本就风里雨里的,遭罪的命。
炕中间热,两头冷。这是一个弱点。庄户人家贤惠的女人起得早,甚至摸着黑就裹了头巾,拉开门,抱起一把麦草,往坑洞里搡。奄奄一熄的灰烬陡然闻到新鲜的空气,精神一振,于是死灰复燃。炕上的孩子们就不冷了,热烘烘的,任凭满院子雪花飞舞,感受最温暖的冬天。
早起的庄户女人还喂猪喂鸡,打扫庭院里的雪。扫帚划过雪地的声音与间或风的啸声混杂在一起,像一曲乡村音乐。
现在在市场经济开放的今天,农村家庭也都富了,年轻人时髦也学着城里人,把炕拆了,双人床,暖气、空调都用上,只有那40、50、60、后们还钟情那暖烘烘的土炕.....。

 Post By:2011/9/7 20:05:30
Post By:2011/9/7 20:05:30


 [本帖被加为精华]
[本帖被加为精华]

 Post By:2011/9/7 20:26:58
Post By:2011/9/7 20:26:58




 Post By:2011/9/7 20:44:00
Post By:2011/9/7 20:44:00




 Post By:2011/9/7 20:57:51
Post By:2011/9/7 20:57:51




 Post By:2011/9/7 22:03:48
Post By:2011/9/7 22:03:48




 Post By:2011/9/8 6:02:34
Post By:2011/9/8 6:02:34




 Post By:2011/9/8 6:32:22
Post By:2011/9/8 6:32:22



 Post By:2011/9/8 9:25:11
Post By:2011/9/8 9:25:11




 Post By:2011/9/8 9:43:11
Post By:2011/9/8 9:43:11




 Post By:2011/9/8 9:50:52
Post By:2011/9/8 9:5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