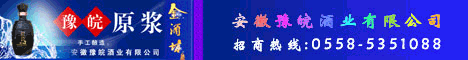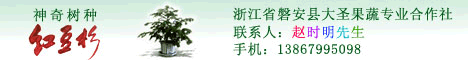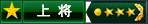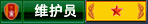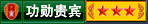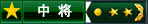宿松方言
家乡话,是最让游子激动的情愫。车站码头,万人躜动之中,忽闻零星半句家乡话,那一定会寻声挤将过去,此谓之“他乡遇知音”。老乡见面,那怕你普通话说得再好,也必改方言交谈,这就叫“共同语言”。游子离乡日久,忽然听到家乡话,那肯定浑身通泰,勾起思乡的情绪,开启记忆的闸门。游子离家时间再长,遇到紧急情况时,家乡话往往会脱口而出,因为那是植入心灵的基本元素。我非常佩服“母语”一词的发明者,一个“母”字,把那种血肉相连的感觉表达得淋漓尽致。宿松话,就是我们宿松人的“母语”。
宿松自古属楚头吴尾,近代系三省交界,南来北往,兼收并蓄,宿松方言中也就既有九歌楚辞中的“刚”,也有吴侬软语中的“柔”。刚起来,青云直上,凛凛威风。小时候,每当村子有人家东西被偷,女主人必定有一番“村骂”,一手拿着砧板,一手拿着菜刀,边剁边骂,那架势之雄伟、言行之泼辣,表达之丰富、神情之生动,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确实可以和任何语言媲美。柔起来,肝肠寸断,缠绵悱恻。黄梅戏就吸收了相当多的宿松方言,所以唱起来柔情百转,百听不厌。特别是《天仙配》中“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那一段,“绿水青山带笑颜”中的“绿”,“寒窑虽破能避风雨”的“避”,必须用宿松话来唱才算正宗,才有韵味。
宿松话其实并不难懂。在新兵船上,我用宿松话说‘塞罗波’、‘倒忖鼠’‘哈巴克’、‘后脑壳’等,接兵的同志大都能听懂,在75师宣传队时,我说‘石头的骨呷,仐草的性格’江苏洪泽战友蔡正林一听就懂。我家那小子‘躲儿’,小时候,调皮玩劣之际,见我面色凝重、准备扬手之时,突然冒出一句“嗯侬不准打我滴滴俄儿”,往往令我忍俊不禁,满腔怒火化为乌有。与普通话相比,宿松方言中的人称代词和称谓确实比较独特,差异较大。一是用“侬”来表示单称,如“我侬”(我)、“嗯侬”(你)、“喀侬”(他)。二是用“几”来表示复称,如“我几”(我们)、“嗯几”(你们)、“喀几”(他们)。三是一些称谓是普通话里没有的,如“父哇、跌跌”(父亲),“姆妈、姨呀”(母亲),“麻妈、待妈”(伯母),“伢伢”(叔叔),“的娘、的妈”(婶婶),“母母”(舅舅),“甲甲”(姐姐)等。特别是“滴滴俄儿”(小孩)一词,把大人对孩子的痛爱、惜爱、溺爱之情,溢于言表,是宿松话里最生动的一个称谓了。
宿松话里有些词语和表达方式比较独特,蛮有味道的。有的话必须倒过来说,才是地道的宿松话,如“热闹”要说成“闹热”,“公鸡”要说成“鸡公”,“母鸡”要说成“鸡母”等。在省建校学习时,宿舍夜聊,一不小心冒出了句“鸡公”,解释后,哄堂大笑。时至今日,还有人来电话问:“你家鸡母可好?鸡小有否?”“鸡小”显然是外县人依此类推的杜撰。有些话在普通话里是有音无字,非宿松人不能听懂的,如“角涅”(吵架)、“挠威”(谢谢)、“塞罗波”(膝盖)、“木里木戳”(笨)、“乌麻焦工”(烧糊了)、“黑里乎子”(傍晚)等。有些话则与字面意思相差太大,望文生义往往差之千里,如“好戏”表示“好玩”,“躲猫”表示“捉迷藏”,“驳咀”指“吵架”,“沙央”则是指“蜻蜓”,“米毛”是说“尾巴”,“马儿”是指“小凳子”,“手服捏子”是指“手帕”,“没得改”则表示“没有办法”。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笑话。土改时,一外地女干部到我们乡下做老百姓思想工作,傍晚时分,准备起身,男主人对女干部说:“就在我家过夜吧”,本意是尽地主之谊,留她“吃晚饭”,但女干部当时满脸通红,回去大骂农民“流氓”。
据语言学家研究,我们宿松方言有六个音调,分别是阴平、阳平、阴云、阳去、上声和入声,这使得我们的言语具有得天独厚的音乐感。试想,现代音乐也就只有7个音调,咱宿松话天然就6个调,这不就是说得和唱得差不多吗?确实,宿松话常常拖一个尾音,这往往体现在一问一答之中,例如,问:“嗯侬吃了么?”,答:“吃着威”。而且这个尾音还拖得较长,中间可能还会变调,有点象乐曲中的和弦,听后使人倍感亲切。这特别是在宿松女孩子说来,韵味丰富,十分动听。在省城学习时,有次在校园遇一女老乡,用家乡话简单打了个招呼,就把和我一道上图书馆的同学听得当场发呆,连说“宿松女孩子说话真好听”,非要缠着我将女老乡介绍给他做朋友。我当时就义正辞严地指出:“宿松水不流外人田,宿松女不嫁外地郎!”那哥们气得很久不和我说话。宿松话里有入声,这就为我们宿松人学习古典诗歌大开了方便之门,这也可能是宿松诗人、词人很多的一个原因吧。现在,全县成立了不少诗词协会,一帮退休老人,用宿松方言,你吟我和,自得其乐,陶冶性情,颐养天年。
说不完的宿松话,道不完的家乡情。宿松话是宿松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我们宿松儿女世世代代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工具,是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宿松人”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我们每一位游子终身不忘的心灵音乐!
女儿在韩国留学时,曾经在QQ空间转载过‘宿松话’八级考试题,更是让人忍俊不禁,择日再发上来,让战友们一笑。

 Post By:2012/9/21 22:43:41
Post By:2012/9/21 22:43:41


 [本帖被加为精华]
[本帖被加为精华]

 Post By:2012/9/21 23:09:28
Post By:2012/9/21 23:09:28




 Post By:2012/9/22 4:53:21
Post By:2012/9/22 4:53:21




 Post By:2012/9/22 6:24:03
Post By:2012/9/22 6:24: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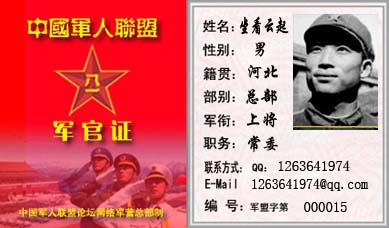


 Post By:2012/9/22 7:35:52
Post By:2012/9/22 7:35:52




 Post By:2012/9/22 8:01:56
Post By:2012/9/22 8:01:56




 Post By:2012/9/22 8:04:42
Post By:2012/9/22 8:04:42




 Post By:2012/9/22 9:11:35
Post By:2012/9/22 9:11:35




 Post By:2012/9/22 9:58:19
Post By:2012/9/22 9:58:19




 Post By:2012/9/22 20:20:09
Post By:2012/9/22 20:20:09